01新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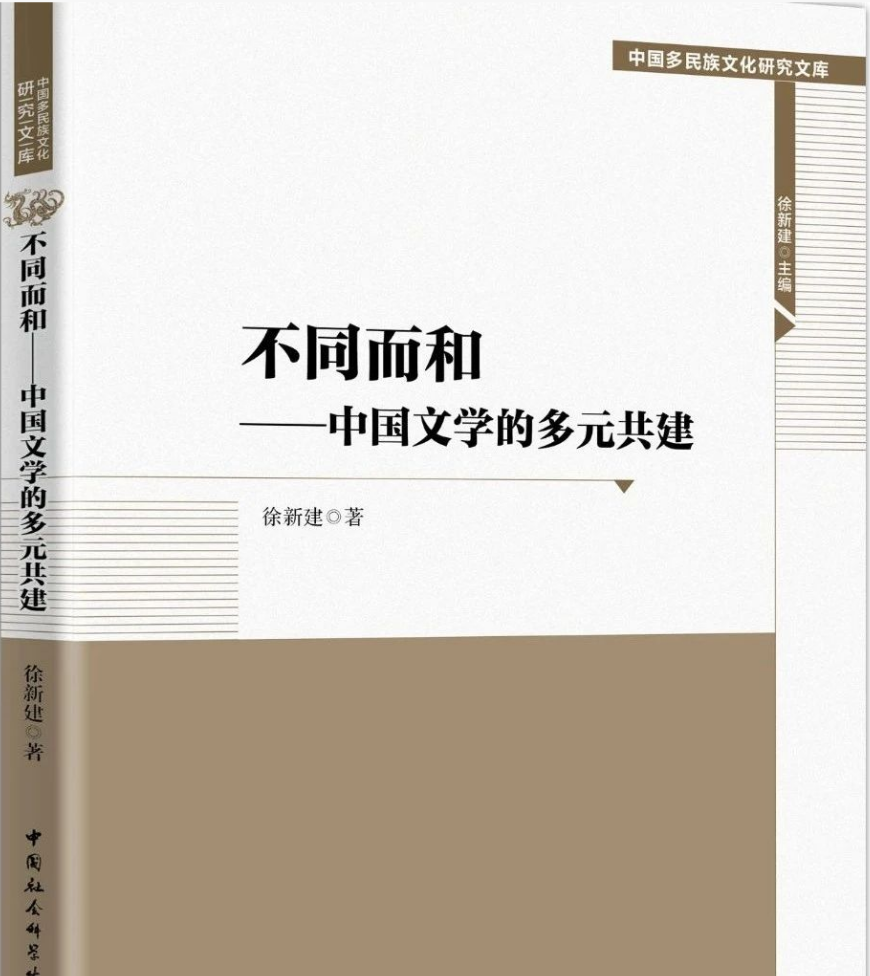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 者 徐新建
丛 书 中国多民族文化研究文库
版 次 202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x 1000 1/16
印 张 33.5 插 页 2
字 数 505千字
定 价 178.00元
ISBN 978-7-5227-1254-3
02作者致谢
2011年11月,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立项。项目的申报和开展得到学界同人的广泛支持,除了牵头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协作单位包括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及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和喀什大学的相关院系。课题组成员分布多元,阵容庞大。十位子课题的负责人分别是:汤晓青、曹顺庆、叶舒宪、彭兆荣、钟进文、姑丽娜尔·吾甫力、阿拉坦宝力格、卓玛、阿库乌雾(罗庆春)和梁昭。作为首席专家,笔者主要承担了课题前期的总体设计、相关调研的组织协调和结题报告的执笔撰写。本书即为结题报告的最终成果。
感谢全国社科规划办的立项支持,让聚焦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课题申报在重大项目的激烈竞标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感谢各阶段评审和参与专家——朗樱、关纪新、朝戈金、徐其超、纳日碧力戈、曾明以及杨圣敏、蔡华、杨煦生、周大鸣、王建明、李晓峰、刘大先、李光一、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宁梅、多洛肯等给予的充分认可及中肯建议。同行专家的支持勉励,使项目的顺利开展获得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感谢调研过程中学界同行及相关部门熟悉与不熟悉友人给予的热情接待和鼎力相助;感谢跨越数十家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课题成员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没有大家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与精诚团结,项目的开展几无可能;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提供的出版资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尤其是责任编辑郭晓鸿博士极其专业的设计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章节曾以阶段成果形式在国内期刊发表,但在集结出版时做了补充修订。书中重要成果均得益于项目组全体成员的集思广益与无私奉献,若有缺憾和错漏则由笔者本人承担。
感谢李怡教授和马克·本德尔教授为本书撰写序言。他们的热情勉励和专业评价令作者备受鼓舞。
作为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基础项目和艰难事业,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阐释依然任重道远,我们都还在路上。
03全书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
一、内外交织的文学变义
二、“英文学”对应下的“汉文学”革新
三、创建小说主导的“文学中国”
四、新词筐承载的新“中国文学”
第二章 华夏崛起:解体王朝的复兴先声
一、1900:世纪之变
二、清末年间的反清浪潮
三、汉族复兴的标志象征
四、汉语世界的小说革命
第三章 解放政治:迈向现代的历史巨变
一、辛亥起义:从独立到建国
二、王朝终结:从分治到共和
三、解放少数:从束缚走向平等
四、苗夷觉醒:解放政治与解放文学
第四章 团结起来:民族联合的多元创建
一、共同纲领:政治协商下的民族联合
二、共同缔造:“非汉民族”的建国参与
三、自主表述:文学世界的多族景象
四、民族团结:联合奋进的时代选择
第五章 立誓结盟:华夷关联的时代象征
一、封贡与誓盟的古今演变
二、歃血盟誓的历史延续
三、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整合
四、普洱盟誓的时代象征
第六章 身份归属:多元民族的政治确认
一、民歌关联的文学族别
二、承前启后的族类认知
三、作为建国根基的民族确认
四、汉语“民族”的多重论争
第七章 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展现
一、形塑认同:民族文化的现代交汇
二、国家运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正式登场
三、民族文学:多重交映的社会工程
四、语文并置:口语和书面的交叉兼容
第八章 母语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语文根基
一、现代中国语、汉藏诸语系
二、族别和语别、口语和笔语
三、民族文字和母语文学
四、语言转用与双语书写
五、多语言政策与多母语前景
第九章 改革开放:多民族文学的再度起航
一、新时期开启新变革
二、新交流催生新跨越
三、新方法带动新话语
四、新范畴创建新体系
第十章 文学生活:民间传统的世代承继
一、《格萨尔》:英雄的颂唱
二、《亚鲁王》:祖灵的回归
三、《阿哈巴拉》:摩梭的传承
四、《阿里郎》:文学的跨境
五、多元美学:构建跨族别的审美话语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序一 置身“问题情景”的学术研究——与新建先生共勉
李怡
四川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副会长
新建兄的学术新著要出版了,来函嘱我完成序言一篇。这让我有点为难,他的研究有很多方面是独门绝技,特别是多民族文学的研究部分。要让我加以评判,可能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是,这些年来,我又的确比较关注他的动向,并且从中获益不少,予以拒绝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思前想后,我只好谈一谈对新建兄治学的粗略印象,也算是我对他即将面世的学术著作的一种阅读心得吧。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新建兄的专业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或者说文学人类学,后者是“自主设立的学科”名称。在中国教育部最早的学科名目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渊源深厚,甚至在一些国内高校,这两个学科就放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从更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分出骨干另建了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因为这一层学科的渊源和知识的关联,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对1920年代“歌谣运动”的研究,因为这本身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那时,我注意到新建兄的研究与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有所不同,有着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路径。到后来,他的重要精力放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我很快发现,他又与某些“补缀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同,在一开始,他就着力挖掘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而不是将它仅仅作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点补充和局部延申。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出现了从思想到方法的重要调整。中国社科院的关纪新老师、汤晓青老师是积极的推动者。他们多次盛情相邀,通知我参加“多民族文学论坛”。后来思之,这包含了他们独特的用意:让更多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走出传统思维的束缚,在多民族文学的“异质空间”中开阔视野,自我更新。事实证明,这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举措。两个“文学”领域同根而生,却在新世纪的前后各有生长的方向。大家重新聚谈,面对面讨论问题,真的收获多多。对我而言,则接受了不少的基本观念的挑战,比如什么是“文学”,我们现当代文学长期沉湎在知识分子的创作之中,以对文人写作的观察构建起了一整套的文学阐释模式。但问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除了精英化的知识分子写作,都还存在着非精英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这些民间的非精英化的文学的重要组成。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些现象,需要用新的观察方式、新的阐述方式来分类、认知,就是最基本的概念——文学就已经如此的千差万别了。就是在这些讨论中,新建兄是十分活跃的一员。虽然不是每一个观点我都同意,但必须承认,其目光的敏锐,问题意识的鲜明和表述的力量,都一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触动我的思索,逼迫我的反思。
在新建兄的这本新著中,第一章就是“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令我想起近二十年前参与多民族文学论坛之时的情景种种,感概良多。对关键词的考察,包括对“文学”这个关键词的历史梳理,在新世纪以后不乏其人,金观涛先生的“观念史”研究更是扩展成了一个闻名中外的著名的数据库。我本人也曾经投身其间,乐而忘返。尽管如此,新建兄对“文学”的考辨依然独到,他自由地穿行在中英日等多种语言文化现场,剔抉清晰,感受细腻,在中外文学比较之中再启多民族文学比较的观察。这种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阐述,让一个论证有年的话题再度焕发了光彩。
这本著作,最大的篇幅是在讨论多民族文学的相关问题,体现的是新建兄多年思索的成果。我相信,这一讨论的最大意义还不在于具体作品的评定,而是一种更大格局的历史认知机制的形成。
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的理念已经逐渐进入到了整个中国文学的讨论当中。如何在中华文学史的大格局中真正体现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事实,如何让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获得自己的主体性,不再因为“少数”而退居文化的边缘,成为汉文化叙述的补充和附缀,学术界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热烈的研讨。阅读新建兄的文字,我还想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中,我们既有的文学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只有从根源上清理了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生长过程,我们才便于实现新的文学的叙述。
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史”的建构和传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而言,在他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有接触任何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框架;而这样的文学史,本身却是在把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视作“少数”之时完成的。以汉族知识分子为绝对主体的文学史书写者本身就不具备更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知识,他们在缺少更充分的多民族文学体验时完成了汉民族的文学史,后来又因为国家文化格局扩大的需要而试图纳入一定的其他民族的内容;而在纳入的时候,整体的文学史框架已经无法改变了,补充与附缀的痕迹在所难免。在最后,当这样一种文学史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文学的权威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加以传输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最根深蒂固的知识系统就形成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样的知识系统都会发生持续不断的作用,成为在社会上最难改变的基本认识。如果说这些现实普遍地存在当今中国文学教育中,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深层调整——比如我们所讨论的多民族文学知识重新进入的问题就尤其显得重要了。对于汉民族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在读者层面产生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一种将理论的架构视作高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思维习惯,对于汉民族以外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则还直接受制于语言与区域的固有障碍。
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毋庸回避的事实是,占人口数量优势的广大的汉民族的读者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语言鸿沟。他们根本无法领略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的魅力,无从获得真切的感性体验。此外,也存在区域文化关怀本身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文学的吸引力来自它能够将我们自身的关怀对象化。我们有机会借助文学的世界发现我们自己心灵的律动和希冀。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往往容易是对自己生存遭遇的“切近”之处发生“共鸣”,产生关注的冲动。作为少数民族区域的独特存在,其社会文化情形、现实遭遇显然与生活于汉地的读者有种种的差异。除了“观看”的需要之外,能够真切地产生应和的所在并不一定丰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地读者了解、认识其他民族文学的“切迫性”。大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语言的焦虑,新建兄特别讨论了“母语表述”的问题,将它视为“多民族文学的语文根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自我生存对象化的镜像。但是,这一基本特征所产生的效果却未必都是一致的。我们既见到了固有自我语言牢笼的保守,也目睹了突破语言边界,寻找文化交流的努力,就如同寻找“陌生化”与自我对象化同样必不可少一样。人类文学的历史既是自我沉醉、自我欣赏的历史,同时又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彼此沟通和认知扩大的历史;而且越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民族就越是希望在未知的世界中寻找异样的文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相反,只有那些封闭狭隘的民族才会陷入到不可自拔的自恋状态,拒绝对其他异样文学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接受。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越是发达的国度,越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这是一种文化的气度,也是一种民族的伟大气象。也就是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占数量优势的汉民族读者其实同样存在着关怀异域世界、体验其他民族经验的愿望和冲动。今天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愿望与冲动,如何有效地生发为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更为深入的体察和认识。更重要的则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在没有更深入更丰富地体验其他民族的文学世界之前,一切文学史的叙述都应该留有余地,等待更多的亲历者的参与。自然,语言的实际隔膜并没有立即解决。不过,我想,这本身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来推动这样的沟通。只要我们突破了目前存在的如此统一的文学史教育的模式,尝试着不同民族区域努力建设自己全新的文学史叙述,并且让这些文学史的新叙述同时伴随着对文学作品向其他民族区域的翻译、推广,使之不仅有其在他民族汉族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也努力促进不同少数民族区域之间的翻译传播,那么在新的一代接受者那里,或许会有比今天丰富得多的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感受和体验。在某一天,当汉族与其他各民族对彼此的创作现状都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之后,一些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才会出现,并且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而且,它不会自命是历史叙述的终点。
阅读新建兄的文字,读者应该不时产生如我一般的感触和心动,因为他的学术讨论从来都不是架空了的自说自话,几乎在每一个主题,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处判断中都充满了对当下学术与思想状况的关切。我将这种切入骨髓般的体验称作学术的“问题情景”。也就是说,他的论辩的冲动总是来自于对当前思想文化现场的浸润;他的提问是对种种“问题情景”的不可遏制的回应。因为回应,他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因为对话,他能够唤起我们精神的回响,激发我们再一次出发的强烈愿望。这,可能就是学术的赋能吧。
我姑且写下这些阅读的感受,当作与新建兄的共勉。
2022年元宵节于成都江安河畔

序二 中国文学百花园:简评徐新建教授的多民族文学新作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
文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专家,出版专著The Borderlands of Asia: Culture, Place, Poetry. Amherst, Mark Bender, ed. (2017. New York: Cambria Press.);译著《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苗族史诗》、《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婚俗志》等。
徐新建教授的新作将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丰富多彩的多民族传统文学及其现代演变。尽管书面文本是几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传统文学却都基于口传。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这种关注,可视为理解源自《诗经》的中国文学传统相对较新的一种途径。这种文学传统从根源上就与口语及歌唱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且反映了不同地域和族群的文学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境内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其历史是一个在多变气候与地理环境中复杂的迁徙、扩张及互动与融合过程。由此诞生了地球上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区域之一。
在19世纪,随着工业化与帝国冒险的发展,中国更多地接触到世界其它地区的知识,最终在20世纪初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了一种比较视阈下的新文学观。在本书第十二章,徐教授讨论了王国维等学者对中国史诗传统“缺失”的焦虑。由此,他们开始寻找“可比物”,并最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格萨尔王史诗的发现打开了一道闸门,不仅从此发掘出了许多史诗,而且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尤其是在1949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史诗之国”,对史诗的研究力度也持续加大。
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拥有一个充满活力且多姿多彩的多民族马赛克。文学作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传统文学,抑或是现代作家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都是更完整的中国文学图景中的一部分。而在过去,中国文学曾被误认为主要是汉族的文学成果。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扩展中,少数民族文学以及不同类型的文学得到承认。在汉族地区,源于地方文化、曾被忽视和低估的口头传统和与口头相关的文学风格也得到认可。此外,某些风格还包括我提出的“史诗毗连”(“epic adjacent”,即将发表)式的表演叙事。这些风格通常具有与史诗相关的某些特征(尽管“史诗”这一术语的意义一直在不断演变中)。这些与“史诗毗连”的传统例子包括:古代敦煌的“变文”、“宝卷”以及中国学者称之为“曲艺”的各种形式的弹词。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众多的多民族文学,它们丰富和扩展了“中国文学”,其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翻译。
徐教授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本书的写作就是从文学人类学的维度来进行的。尽管与文学研究中的民间文学、生态文学、比较文学、民族/原住民文学研究存在类同,文学人类学在中国以外的追随者却有限。事实上,中国现有一个特别活跃的文学人类学领域,学者们正努力为研究中国多元的文学及文化做出理论贡献。徐教授认为,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文学文本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涉及多个参与者”。文本的这种生命,徐教授称之为“文学生活”。这是我们理解以传统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关键,无论对多样态的汉族文学传统还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都是一样。
与西方民俗学“表演学派”的学术观点相呼应,徐教授认为将文本视为嵌入生活的文化过程至关重要。为了解释文本,人们需要融入它产生的背景。这种态度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顾颉刚以及后来的钟敬文等学者提倡“到民间去”,搜集口头文学。正如徐教授注意到的那样,早期的调查工作带动后来数量庞大的民间文本的搜集(到1980年代,中国学者搜集的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的字数达到数百万),但这些文本往往缺乏对与文本相关背景的关注。我记得自己研读过许多在1980年代出版或再版的民间文学文本。这些文本收录了许多民歌或民间故事,有时文本也会附带故事讲述者/歌手、采集者姓名、采集地等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单独发表的著述中会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例如马学良和今旦于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就提供了全面的背景介绍和注释,甚至附有几段带拉丁化拼音的苗语史诗。幸运的是,中国学者对这些文本的语境价值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在包括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在内的学者那里得到体现。他们开展了众多有关中国史诗传统的研究项目。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在对口述和较少被认可的文学传统的认识和鉴赏过程中,中国学者明显增加了对这些文献的学术研究和翻译。近年来,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云南和四川的民族出版社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机构出版大量的少数民族史诗、民间文学双语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学术研究。
这些出版物在中国提高了民族文学的知名度,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认可。当然,由于面临语言障碍以及提供阐释框架的挑战,要获得世界对任何类型的中国文学的关注始终面临巨大挑战。虽然某些作品如《道德经》、《孙子兵法》,以及较小范围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电子游戏)在中国以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大部分翻译作品仅仅被学者消费,受众有限。在少数民族的文学世界中,在西藏及周边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可能是最有名的传统文学作品,而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或许是少数民族作家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取得进展。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度比20年前高了很多。这体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也有国外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歌曲和史诗的翻译版。在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举措来改善这种状况,为中国学术和文学作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反映多民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它能在文学的园地里百花盛开。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多语种翻译团队以及发行营销渠道之间的协同工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一个非常成功的非西方作品的例子(即在作为文学标准的《荷马史诗》的压倒性影响之外的作品),是来自中美洲的玛雅圣书《波波尔·乌》(Popol Vuh)。该作品基于一部在18世纪早期转录而成的西班牙语手稿呈现,但长期被遗忘。其完整版本直到20世纪中叶才得以出版。现在,其文本以多种语言(包括汉语)出现在众多版本中,不仅被视为传统史诗文学的典范,而且与古老的玛雅遗址和多彩的玛雅活态文化相结合,引起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想象,从而推动了危地马拉乃至整个中美洲玛雅地区的旅游创收。然而要达成这种认识,唯有通过专门的国际研究人员、翻译人员和出版商在国际出版市场中进行持续合作才可能得以实现。
徐教授在呈现多民族中国的文学花园愿景时,主张“文学不是对生活的反映,文学就是生活本身”。他从丰富的备选项中选择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学的许多例子,首先对由几个少数民族共同分享的藏族格萨尔史诗的不同版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接着讨论其它北方史诗传统,以及最近才被“发现”的南方和西南史诗传统。自1950年代以来,这些传统日益受到重视。更早的时候,像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这样的外国学者以及民族语言研究先驱者马学良这样的中国学者都曾对此给予关注。徐教授详细讨论了苗族、纳西族(摩梭人)等人群的口传文学案例。他建议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构建每个文学项目,强调提供背景并注重上下文,以充分了解它们各自的性质和优点。这种方法需要完整的专家团队(和适当的机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需要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理想的情况下,该方法将包括来自语言分析、诗学、翻译研究、民俗学、民族音乐学、互文研究、博物馆展品及私人收藏研究等各方面获得的理论与实践。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必须在传播地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和进行活态传承,还要有本土学者和健在的传承人(如果有的话)参与其中。
需特别指出的是,流传于黔中苗族地区的亚鲁王史诗/仪式,其传统在本世纪初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涉及到地方文化、自然生态及历史背景等多个维度。与其他许多史诗学者的看法相同,徐教授强调,尽管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人们拥有了大量通过音译和意译形成的书面记录样本,然而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唯有保持活态的传统表演,史诗才能以多种形式持续存在。以苗族的“亚鲁王”为例,传统口头表演的可行性,依赖于对“东郎”,亦即民间演述传承人的培养。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中传承本土文化。
学者们一般会将这样的传统描述为“史诗”/“仪式表演”,因为这种丰富的传统同时兼具这两个术语的相关特征。关于史诗的范畴,徐教授根据其它几部西南创世史诗的内容提出:这一术语现在包括了现今标准的“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两种类别,以及由这两者叠加而成的第三类别,即“英雄创世史诗”。属于此第三类的不仅有《亚鲁王》,还有《苗族史诗》、彝族诺苏人的口传史诗《勒俄特依》及主人公与标题同名的壮族史诗《布洛陀》等,里面都有英雄人物,或者是被芬兰史诗学者劳里·杭科(Lauri Honko)所称的“典范形象”(exemplary characters)。
总之,徐教授的目标不是试图人为地“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价值,而是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美学,使特定传统的独特特征能够通过适当的文化术语得到鉴赏。虽然在对各种传统的不断演变的鉴赏模式之间肯定存在关系和共鸣,但有趣的是我们会看到更大规模的全景美学,其或许将最终带来徐教授设想的“不同而和”的多民族、多美学空间。
我认为这样的设想完全可被世界所接受。
(文培红校)

后记
十年了。
记得那是2011年的秋天,通知到北京答辩。一同参与的还有彭兆荣教授投标的另一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探索”。我是课题组成员,应首席专家之邀,作为两位“辩手”之一进场答辩。我主持投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搭档是汤晓青,地点都在京西宾馆。同一时间内竞投标的项目很多,在宾馆进进出出,遇见的学界熟人不少,文学组就有新疆大学来的王佑夫教授。他报的项目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不过时间匆忙,各项目几乎都是差额录选,气氛比较紧张。大家顾不上交谈,只在楼道上、电梯间打打招呼,擦肩而过。
入场答辩的情形还依稀记得,具体问了什么和答了些啥,几乎都忘了,大概全部要说的就是阐述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时代背景、论证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我们课题组为此做了哪些认真准备。
后来结果公示,我们的项目中了,连同彭兆荣和王佑夫在内的一批。
接下来,开题报告通过,而后便开启了东南西北的实地调研和咨询论证。东北去到赤峰、延边,西北抵达喀什、伊犁;西南走得最多,川滇黔桂几乎每年都去。2013年起参与创建川大牵头的2011学术平台“中国多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凝聚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成员多与项目组重合,故每每举办研讨或实地考察都一并推进,议题交叉,人员结合,时常是阵容浩浩荡荡,气氛热闹不已。那时节的学术氛围真好。大家来自天南地北,族别各异,却亲如一家,相见恨晚;聚会时直抒己见,开诚布公,即便能为学理分歧争得面红耳赤,说完后即刻和好如初,无有芥蒂,其乐融融,真可谓融入了多民族研究的最佳时期。
2018年末,项目组与协同中心联合出行,组织部分成员考察云南红河与玉溪。一则补充滇省多民族文学的现实材料,一则对已完稿的结项报告做打磨研讨。考察采用流动工作坊形式,沿路而行,边走边议。到达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蒙自后,在阿库乌雾与云南朋友的联系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国立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旧址与滇越铁路的碧色老站。在元阳菁口村,除了观看远近闻名的梯田景观外,还与村民座谈,了解村里与高校合建民族文化基地以及旅游开发的基本情况。望着哈尼族村民在田间地头劳作与屋前屋后操持民宿接待的辛劳身影,令我想起了泸沽湖瓦拉别村。在那里,我曾与蔡华、梁昭等一道,静静地倾听和记录摩梭民歌“阿哈巴拉”的颂唱。在那里,远离了繁忙交往和网络便利,也远离了琐碎杂务与都市喧嚣。紫色的索玛花开在房前屋后,潺潺溪水在四处泛着亮光。我们整天与村民彭措尼玛一家待在一起,相互的交谈亲切自然,发自内心的歌声则显得自在且不可或缺。
回想起来,自立项以来的年年月月,我们的教学科研乃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那些跨越春夏秋冬的日子,与其说是校园书斋的机械延续,毋宁说已变为进入多民族田野后的解放身心。在天南地北的高山峡谷里,在民情鲜活的村寨场景中,让我们身临其境感触和感动的,是文学生活的动态展现与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
汉语的古典美学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由此连接一个世代相通的道理:文学就是生活,生活因多样而美。
古往今来,能拥有不同而和的多民族文学生活是一种幸福。
2022年除夕-成都望江路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