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好,刚才张西平教授讲了“要创造中国的翻译理论”,我刚好接着他的话来讲,我的题目是《翻译变异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2013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此书可视为国际文化传播和翻译变异的中国话语。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变异学理论,其实也是翻译理论,名为“变异”。这是我们中国学者提出的创新性中国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所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变异学正是提出了创新性的中国话语,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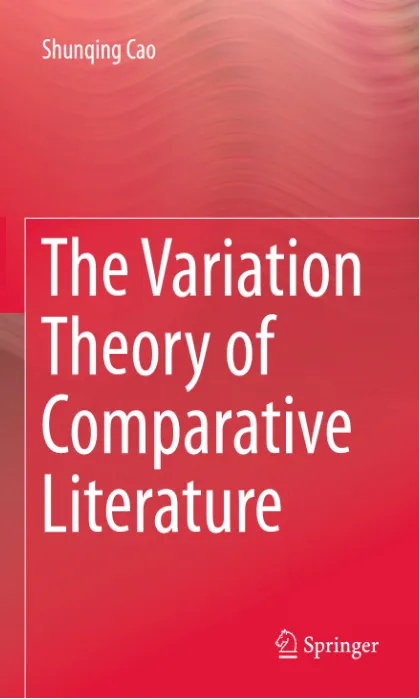
例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主席佛克马教授(Douwe W. Fokkema)亲自为此书作序,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发现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且完全有资格完善这些不足”。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顶尖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评价这本书对跨文明、跨文化的研究超越了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beyond the simplistic Huntington-style clash of cultures。这个评价太高,我不敢当;但是能得到达姆罗什这样的评价,我也很高兴。
达姆罗什还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中研究了我在变异学理论里提出的跨文化交流中的失语症(aphasia)、异质性(heterogeneity)、中国特色等问题。时间所限,就不具体展开谈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PPT。
另外一个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德汉(Theo D’haen)认为,《比较文学变异学》必将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他评价此书:“The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等人写了一本书,名为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这本书的第50页引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部分内容,阐明变异学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另一个必要的比较方向或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
法国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材中专门介绍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跨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那么变异学是从哪里提出来的?变异学是中国智慧,是基于中国传统的思辨智慧。大家都知道,《周易》是谈变易的,但“易一名而含三义”,有易、有不易、有简易。钱钟书在《管锥编》的开篇“周易正义”里就研究这个问题,研究通了后,他就回过头来批评黑格尔。黑格尔说中国人没有思辨,什么才有思辨呢,德语才有思辨。黑格尔举德语“奥伏赫变”(Aufheben,可意译为“扬弃”)为例,“奥伏赫变”一词而含相反之两意。但是钱钟书说,我们的“易”,一字而含相反之三意,黑格尔无知,完全没有认识到我们中国的思辨思维。易、不易、变易,恰恰是我们今天搞文化交流、跨文明交流和翻译研究最重要的思维视角和结构规律。在翻译的变与不变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简易的基本规律。发现这个规律,将极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的复杂而又可以把握的规律。
变异学追求的是“异质可比”,同样,文学翻译也可以从“异质可比”中去“获得”翻译过程中“失去”的部分,这一视角不仅可以重审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更可以重审“翻译文学”究竟是作为外国文学还是本土文学等等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剑教授,他认为变异学是中国学者的一个理论创新点。
变异学能解决哪些问题?尤其是能解决翻译理论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我简单总结了四点:一、学术界现在谈翻译理论争议最大的问题,即创造性叛逆的问题、翻译文学是否外国文学的问题;二、从阐释变异的角度来看不同文明的阐发和互鉴问题;三、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四、西方文论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等等。
我们先来谈一谈翻译变异与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若干问题。变异学启发了国内翻译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翻译家已经奉献出了不少很忠实于原文、也堪称优秀的译本,但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怎样改变这个现状?变异学可以指导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策略和实践。变异学通过让人们看到并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并非原作简单的翻版,从而引导研究者跳出传统翻译路径,关注翻译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独特境遇及左右译本命运的变异因素,进而推动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长期以来,不管是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很多人坚持绝对忠实,也有很多人坚持忠实是不可能的。学术界在翻译的差异性和不可译性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早期西方翻译理论中有“原文至上”“原文主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此处就不展开讲了。至今仍然有中国学者坚持忠实派翻译。谢天振就曾撰文批评过这种观点,他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话,并对之进行质疑。一些学者说:“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诉求,也不是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文学类别的诉求,而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的他者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诉求,任何对文学和文化的曲解、误读和过滤都是与这一根本诉求相违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允许你们误解、曲解、误读,总之,就是反对不忠实。这些学者还举出作家高尔泰坚决拒绝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不愿自己的作品受到翻译的“文化过滤”的例子,对此种张扬民族自尊的“壮举”颇为赞赏。而谢天振则说:“我感到疑惑的是:其一,世界上存不存在没有文化过滤的文学、文化翻译?其二,高尔泰的作品最终有没有不被‘文化过滤’地‘走出去’了?”当今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巴斯奈特(Bassnett)认为,翻译没有办法不误读,异质文化仍然是可译的,它的不可译性只是暂时的相对不可译。
谢天振提出了一个在翻译学界影响很大的理论“译介学”。他反对原文至上,认为简单地套用“译入”思维、视忠实为翻译的唯一标准、主张信达雅,其实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中国建国初期即创刊的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期刊,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后推出的‘熊猫丛书’和目前仍然在进行的‘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和出版,其翻译都严格遵循了‘忠实原文’的准则,翻译出来作品也都最大限度忠实地传递出了原文的信息,然而其中的极大多数外译作品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个中原因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吗?”甚至我们的《中国文学》期刊已经停刊了。
我部分同意谢天振的看法。文化固有的差异以及文明之间固有的异质性导致了翻译的变异,这是不可避免的,原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免要经历译入语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而再生。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文学文本将经历多个层次的变异:包括语言层面,词语的变异、句式的变异、修辞的变异等等;文化层面,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需要被恰当解释或转换,以避免文化隔阂;审美层面,原作的艺术风格、情感基调、象征意象等需在译文中得到尽可能的保留与再现。翻译的变异建构的是健康、动态、活跃、变化的世界文学生态,文化的国际传播必然有一个变异过程。没有翻译的变异,就没有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实际上,任何民族、国家要达到对外来文化的准确理解与全面认识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就是一个变异的过程。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的原文是诗体,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指责朱生豪的散文体翻译“曲解”了莎士比亚原文的文体,从而否定朱译本的价值与意义呢?包括严复译《天演论》,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也部分不同意谢天振的看法。谢天振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有人说是中国的翻译理论,但其实它并不是中国的。谢天振引进的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的关键”(“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谢天振将其引进后,创造成译介学,现在已经被写进了很多教材里。我们现在一讲翻译,就讲译介,就是谢天振的译介学。但是“译介”在中国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忠实派”和“叛逆派”之争。目前,对创造性叛逆主要持两种观点: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者认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回避的事实;反对者认为其与翻译的忠实性标准背道而驰,是在鼓吹误读、误译,并且导致了近年来图书翻译质量的下降,造成了译介的混乱,比如许钧教授就很担心这个问题。
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那么所有的叛逆都是创造性叛逆吗?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批评。王向远就说:“所谓‘翻译总是创造性的叛逆’,显然只是一种印象性概括,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断,翻译确实免不了‘创造性叛逆’的成分,但并非‘总是创造性的叛逆’,如果一多半的字数都属于‘创造性的叛逆’,是否还算是合格的翻译呢?在‘创造性叛逆’之外,有没有‘破坏性叛逆’呢?如果‘破坏性叛逆’的比重多了,还能叫做‘创造性’的叛逆吗?如果译文基本上是原文的忠实转换和再生,那它是‘叛逆’原文的结果,还是‘忠实’原文的结果呢?”由此可见,创造性叛逆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创造性叛逆”,这个看法是外来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中国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谢天振在世的时候对此进行过反省,他的反省是什么呢?他说,大家不要误解,“创造性叛逆”一语是英文术语“creative treason”的迻译,是一个中性词,“创造性”一词并无明显的褒义,“叛逆”一词也无明显的贬义。他的意思是说,这里使用的两个词都是中性词,并不是所有的译文都是叛逆。但是他本身就是这样表述的。
学术界的批评是否像谢天振所说,仅仅是对词语的理解不当呢?显然不是,因为无论是法国学者提出来的、英文中的“creative treason”,还是中文的“创造性叛逆”,意义都是很明确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人会相信,“创造性”一词并无明显的褒义、“叛逆”一词也无明显的贬义。用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翻译的本质,不被误解是不可能的,不被批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王向远所批评的,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所谓“翻译总是创造性的叛逆”,显然只是一种印象性概括,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断。
我认为,用外国学者不妥的表述来创新比较文学翻译理论,出现那么多误解、产生那么多批评,是必然的!我组织编写的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其中第三章“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是由谢天振撰写的。我们有很多教师反映说:“曹老师,看完你们的书,我们的书都没办法教了。”我说:“你们怎么没办法教?”他说:“我们讲翻译,学生译错了,我们批评学生,学生说,‘老师,这是创造性叛逆’。”这就是翻译学的困惑——乱翻成了创造性翻译,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变异学理论就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翻译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如果从语言翻译变异的角度来看,或许情况会不一样。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翻译变异与世界文学的流通变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议题已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尽管众多的中国文学外文译本致力于以严谨忠实的原则重现原作,然而却在“走出国门”的时候遭受到意料之外的冷遇。为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由国外译者操刀的版本,尽管在准确性与忠实度上有所欠缺,甚至不乏对原文的增删与改写,却可以使中国文学中的经典甚至是非经典走向世界文学之列。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文学翻译的成功并非仅仅取决于译者的精确再现,还须深谙比较文学语言翻译变异的变异学之原理,顺应文化与文学“他国化”变异的内在逻辑。换言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应关注其覆盖范围的拓展,更需聚焦于传播深度的挖掘,而这无疑离不开对文化固有差异的深刻理解与对文明异质性的尊重。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并不是全部变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既坚持“本土化变异”原则,又比较忠实地传播我们的文化典籍呢?事实上,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化进程,已经充分证明了翻译变异的价值。
下面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红楼梦》的翻译。刚才说到杨宪益的翻译,《红楼梦》的英译本,最好、最准确的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在西方还有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向来以准确、忠实著称,然而据有效调研显示:“在对《红楼梦》英译进行阅读的有限的普通读者中,霍译本的声望是杨译本所不能企及的。”为什么准确忠实的译本不受欢迎,Hawkes的译本却受欢迎呢?我把《红楼梦》拿来看了一下,在此给大家展示两个文本。例如这一句:“贾母一见着黛玉,便'心肝肉儿叫着大哭起来'”。杨宪益就很忠实地翻译为“Dear heart! Flesh of my child!”说的是“我的心(heact)、我的肉(flesh)”,西方人听了,接受不了;霍译本直接将原文改了,不用这个“心”和“肉”,而是说“MY PET!”“MY POOR LAMB!”“我的宠物、我可怜的羔羊”,这样翻译虽然变异了,但是西方人更加能够接受。这就是翻译的变异效果。
另外,《红楼梦》讲“红”,杨宪益都是翻译成中国文化中的“红”,但是Hawkes却极力避免“红”,因为“红”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里是不一样的。“红”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的是喜庆、热烈与激情;而西方文化中,的“红red”,却指向愤怒、危险与流血。杨宪益把“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怡红院”为“Happy Red Court”,怡红公子为“Happy Red Prince”;而Hawkes在翻译“红”时,往往刻意避开红,在必须翻译“红楼梦”时,迫不得已使用了“the dream of golden days”或者“the dream of golden girls”,“怡红院”和“怡红公子”没有办法避开,便干脆以“绿”取而代之,“怡红院”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为“Green Boy”(绿公子)!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孤儿》。它也是翻译变异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点例子。大家知道,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我们的元杂剧中根本排不上经典,但是由于翻译得法,经过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人的翻译,最后被伏尔泰改编成了《中国孤儿》,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但如果去看他们的改编,你会发现,改编后的文本已经和中国的文本不一样了。对中国观众来说,《中国孤儿》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但是对于法国观众而言,中国的道德精神在《中国孤儿》中处处得以体现,经历了跨国、跨文化横向交流变异的《赵氏孤儿》又返回到中国,成为中国作家的他山之石,使得这部元代杂剧在中国现当代不断被改编和演出,从而获得了新生。虽然《赵氏孤儿》在元杂剧中没有成为经典,但是由于这种交流变异,它却在世界文学中成了经典。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经翻译到中国逐渐变异,最后生成文化新质,形成了中国的禅宗。禅宗已经不是印度佛教,而是中国佛教,我提出的变异学称这种变异为“他国化变异”。即通过这种变异,外来文化经由本土化,逐渐成为了另外一种创新性的文化,甚至是另外一种新文明,但是它仍然保有原文化和原文明的基因,这就是文明互鉴的精彩之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已经跟印度强调语言修辞的规则不一样了,禅宗讲直观的“悟”和印度讲“因明”逻辑也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变异是事实,对这种事实的理论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变异学。可见,变异学不仅仅能够解释翻译的变异,更重要的是能够解释文明互鉴和文明新质的产生和形成,能够指导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
翻译变异作为翻译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力量,其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受到欢迎喜爱,传播得深。文化的固有差异与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这一跨文化活动必然伴随着变异,基于“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变异学理论带给翻译研究的理论启迪就在于“翻译变异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理论视域下如何把握翻译过程中的忠实性(信达雅)和变异规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实现中华文化翻译和国际传播,以及实现中华文化深度他国化的关键问题,也是文明互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问题、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学如何翻译和如何创新的中国话语。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教育部特聘教授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